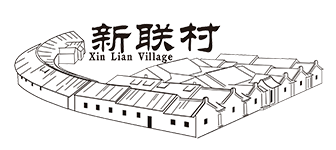刘钦伟
文学,是文化涵义的载体。作家程贤章对此认识是不含糊的。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围龙》,取材于客家生活。他的勤勉,他的睿智,就是要探讨客家文化的涵义。客家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关于客家学研究,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争论,可是对其文化涵义的解释,仍然处于一种朦胧微明的阶段。老实说,关于客家人本质方面的真实是很复杂的,它很容易滑掉,非常难以捕捉,每个人只是“解释”早已存在于自己心中的印象。我感到,程贤章在这种神秘区域进行探索,没有任何教条诱惑他,也不是去作徒劳无益的概念化说明,他的任务是要在人文世界里找到新的以前未被发现的特点,客家文学的丰富性就在于它取多样化的倾向,而多样化正是文学的家园。
从《围龙》的后记可以看出,作家的原始意图就是模模糊糊的,意图起的作用,与其说是计划的作用,不如说起酵母的作用。他的生活,对生活喜怒哀乐的记忆,构成了一种储备,就像檀物胚胎中的蛋白质一样,植物正是从这里面获得养料,以转变成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长大成林。在具体上取胜,这是程贤章的宝贵之处。他是讲故事能手,可他依然把人物作为小说的核心,为此他采访了许多人。如同传说中偷东西的喜鹊,抓着珍贵的东西之后,就把它们藏在窝里一样,积累了谢晋元、黄梅兴、姚子青等人的脸形、轮廓、语言,还有传奇的经历。留在记忆里,而不会像在别人那里很快消失。他需要做的就是唯一能够允许的综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概括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个"成为普遍的形象。"进士第"里的人物,如程武及儿子天送,虑构的成分比较多,他们所以立得住,是因为有一种精神的氛围。有别于抽象的说理,氛围主要诉之于感觉。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他们氛围里有些悲剧的、雄壮的东西,同时又洒上了想象的、奇妙的色彩。应该说,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对待人物和情节是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不仅失去了预测人物未来的权利,而且不给人物下定义,是人物自己在经历的事件中,通过语言和行为说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作家本人尚能掩饰地存在于作品中,但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时不时在夸大一下某一种感情、某一种情欲,以使我们更好地审视他们。他的聪明之处,即是将这些人物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充分展示他们的性格,并使所有的命运都能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得出某种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见到的教益。无比丰富的重大事件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一如整个天空的雷电聚集于避雷针的尖端,自然会产生紧张的效果。人世上无数的时间流水般过去,方始出现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时期,一个人文上星光璀灿的时辰,这就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围龙》通过"进士第"百年的沧桑的描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进士第"的前辈及后人在戊戌变法、东征、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淞沪大战中,以及在以后的土改、合作化、四清、文革、改革开放的种种表现,用一种带有书卷气的说法,即是浓缩了客家的人文精神。客家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文世界,它为数百上千万存家人的热情所激荡,既恒定又流动,既世俗又神奇,它同时又有主流与支流之分。有学者提出"宣传主流文化,才能弘扬客家精神,为后人树在榜样和目标",我是非常赞同的。主流文化"含金量"高,代表一种向上的精神,给人一种人生的坐标。生活是无限运动的经验,人们只要不怀疑有方向和目标,就不会绝望,就会有所作为。
我曾经将《围龙》所揭示的客家精神概括成几句话:爱国爱乡,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勤奋节俭。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当我重读《围龙》后,觉得这种贴标签的做法虽然证明了客家精神的特征,却与其他的地域文化没有明显区别,而且常常混淆不清,犹如一顶帽子你可以戴,他也可以戴。在《围龙》里,客家的文化、精神,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地包围着我们。作品的人物呼吸的就是这样一种空气。程武是作家着力塑造的人物,他与田氏有染后,留下了小生命,逃到老母山当道士,在山上还曾令过夜的香客"侍寝",下山之后加入了北伐军,后来在江西也剿过共,最后战死在抗日的沙场。他的一生好像是一句玩笑话,不但走了火儿而且还不大体面。尽管如此,作家对他的态度还是客观、公正的,既不护短,也不抑长。他的长处,就是早早立下了从军志,即使在老母山他也要看本县城出版的《日日新闻》,而且天天苦练轻功,为了加入北伐军他改名换姓与程潜将军套近乎,汀泗桥和贺胜桥之战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淞沪大战他血洒疆场化作英灵。程武和黄梅兴、谢晋元、姚子青一样都有家学渊源,又进过新学堂,本是一介书生,却胸有大志,国难当前,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惜以身殉国。程贤章的小说写到这里,已超出功利和狭隘的价值评判,不受世事带来的主题限制,而进入了思想文化的探求。对于一种文化怎样看以及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往往不是取决于观看者的立场,而是取决于他的心灵质量。正因为他有一颗自由的心灵,不在作品中包揽一切,而是静待作品和生命的成熟,才使到小说的情节是那么复杂和引人入胜,使人沉迷于其中而不知它要通向一个什么结论。
程贤章的兴趣就是讲故事。他在写作的时候,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在《围龙》中,故事以连环套式的结构展开,故事里有故事,而每一个故事又不是单向发展,它是多样的、多方向的。这里涉及的是真实性的问题,而不是可以让人坐享其成的现成公式。在他看来,真实的含义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随刻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这是因为偶然性普及化的缘故。所谓偶然性是指那些人们找不到前因后果加以说明的事实。程武的一生,不就因为那只忽隐忽现的黑猫而改变了命运。陈家从不养猫,这只猫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要往孩子的被子里钻,难道那就是怪物投胎?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可它却给小说带出一连串的故事和人物。若不是陈老爷看过那么多玄怪小说,那么迷信,程武就不会被抱出陈家。若不是熊村有比国法还严厉的族规,程武与田氏也用不着生离死别。若不是宗族定有"私婚"和隐藏"私生子"的罪名,梁酉生也无须避难于南洋。客家是迁徙的民系,躲不了就走,而走的大多是男人,女人走不了就只好忍耐。田氏和娟妹,是作者笔下很有血性的客家妇女形象。田氏怀孕了,程武求她堕胎,田氏边哭边说"你有勇气,就拿把菜刀立时把我杀了。留下的血脉,舍命我都把他抚养大。"孩子出世的时候,田氏自己接生,并给孩子起了怪有意思的名字——田天送。娟妹与酉生还未结婚,就抚养起出生才三天的天送,而自己在酉生走后七个月,也生了一个女孩,取名醒莲。她一个人卖柴卖菜,就是要把两个孩子送进学堂。后来这两个孩子由伯父陈长修托水客带出南洋,长大后结为夫妇。"重返进士第"和”枫桥祭”,写他们追思往昔,先祭天后拜祖宗;写他们设想未来,要报效土地福荫乡梓;都被一种诗意的气氛笼罩,这是一种美妙的神秘。
说实在的,我读《围龙》时完全陷入一个方向莫测、时隐时现,随时发生问题的世界之中,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可我从那萦绕不去的氛围中,终于看出了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始意图,那就是他掩抑不住的精神诉求和思念故土的情怀。与过去的创作不同,他现在展现给你的不再是一个完整固定的意义,而是在邀你到他作品中去并发现体会深藏其中的涵义。不用担心读者会不耐烦,他有这种自信心。他心里清楚得很,不去研究人物性格,不去写某种环境,不去分析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揭示文化的涵义。在小说中,许多细节描写,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客家人所为,比如祖先南迁的时候,要把先人的遗骨包好带上路,这是因为感觉到这一走就不会回头的啦。娟妹送别酉生时,毫不犹豫将长发剪下让酉生随身带走,是她意识到这一别不知何时能相会。田氏生一婴儿,一看是男孩,就吻遍婴儿的脸颊、小手、双腿,这是她明白男儿志在四方,会有出息。陈长修身居海外,托水客接天送出去,还不是想到天送是"进士第"最后一根血脉。娟妹再穷再苦也要让天送有书读,天送从南洋回乡第一笔捐款就是重建枫桥小学,这与祖先的尊师重教是一脉相承的。文章写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客家文化的问题上。我至今仍觉得迷迷糊糊,笼统地说它是历史的积淀,是文明的标志,摸不着又挥不去:它是矛盾的综合体,有世俗的一面,也有神奇的一面,存在于大地,又羽化为彩虹。《围龙》以客家生活为题材,以人文关怀为旨意,既有精神的飞扬,又有深入事理的认识,它所涵盖的客家文化除了有一种大地的意义之外,还有一种彩虹的意义。正因为这样,它被誉为开客家文学先河的一部长篇力作,而程贤章本人也被第十四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评为对客属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这对于他和他的作品来说,都是实至名归。我在这里要重复一个童话故事里的话"把劳动投入土地吧,土地是不会哄弄你的。"我相信,程贤章耕耘着这块土地,来年的丰收将更加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