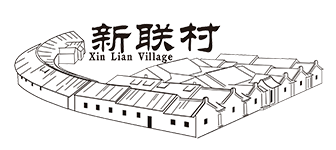一、程贤章:当代客家文学的拓荒者
今年八月,我应全国文学创作广东中心和花城出版社的邀请,参加程贤章长篇小说《围龙》讨论会。这次讨论会规模之大、出席的作家学者层次之高是罕见的。在广东大厦会议中心,数百人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北京、上海、广东、香港、澳门各大报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张炯以及著名作家学者吴泰昌、缪俊杰、刘斯奋("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国凯(广东省作协主席)、郦国义(《文学报》总编辑)、左多夫、蔡宏声等参加,我有幸作首席发言。我在发言中作了这样的论述:在大陆客籍作家中(客家人)有两位代表人物:陈国凯和程贤章。他们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两者是有所区别的,陈国凯长期生活在广州,由于都市文化对他的熏陶;从工人到作家的坎坷阅历;底层生活对他人生的影响;等等,他的作品多数写工人,写人生,鞭挝恶势力,辛辣嘲讽官僚主义等等,作品的背景是工厂、广州大都市的迷乱生活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没有客家文化背景可谈,因而他的作品不属于客家文学范畴;而程贤章少时从南洋归国后,一直在客家人集中居住地梅县生活、工作。他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记者,当基层干部,对客家山村、民情风俗,对客家地区的变化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客家山村为背景的,反映客家人的精神风貌,所以他的作品是道地的客家文学。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程贤章是当代客家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在文学史上,客籍作家和客家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张九龄的诗流传千古;近代诗人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的诗篇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现代作家中张资平、李金发、温流、黑婴、任钧、杨石、碧野、黄谷标等人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在台湾的客籍作家中,钟理和是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有着广泛的影响。到了当代,由于大陆风云变幻,难以捉摸,再加上客家地区的社会关系复杂,大部分客家人都有海外及台港的亲属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动荡年代里,客家人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自顾不暇,"文化之乡"产生不了文人学士,在这几十年中客家文学几乎空白,这是历史给客家人及其文学创作留下的不可磨灭印记。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势头迅猛,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发生了急速变化。有着深深的历史创伤的客家人——无论远居海外或台湾、香港等地的客家人,还是海内的客家人,都怀着报效祖国、报效乡亲父老的愿望在客家地区投资办厂、兴办学校医院;筑堤修路,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使客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新生活面前,程贤章以欣喜心情投入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去,他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思考生活、评析生活、表现生活。从感性的具象到理性思维,程贤章感觉到对眼前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应加以展示。于是,这位在五十年代以《俏妹仔联姻》驰名的老作家焕发出创作的青春风采,写下了国内最早反映农村改革开放,引起人们心灵变化和社会关系重新整合的中篇小说《彩色的大地》,嗣后又创作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客家山村传奇般的故事《腮脂河》,这部长篇小说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到了九十年代初,程贤章老树绽新枝,令人刮目相看,连续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无悔》、《神仙?老虎?狗》和《云彩国》,今年又出版了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围龙》。程贤章连续出版反映客家地区生活的长篇小说,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连续召开关于他的作品的讨论会,海内外报刊连续报道和评论"程贤章现象",学者们更着重研评程贤章笔下的客家地域的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通过这特殊的地域文化所反映出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轨迹。
如果把程贤章的作品串起来读,我们可以看到粤东客家山民历史前进的步伐。《俏妹仔联姻》和《青春无悔》写的是五十年代农村普通山民及普通的基层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的酸甜苦辣,鞭挞了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带来的社会阴暗和丑恶现象;七十年代初创作的长篇小说《樟田河》印数达五十万册,它反映"文革"那段荒唐年代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给人们留下了值得回昧的社会历史资料;《神仙?老虎?狗》及《云彩国》所揭示的是当代中国摆脱了束缚生产力的计划经济桎梏,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下,客家地区人民的勇于冲破旧观念,打破旧程式,积极进取,敢于开拓的精神风貌、而新近问世的《围龙》则是一部颇有气势的"客家人的历史",写出了客家这一支特殊的汉族民系坚韧不屈、敢于斗争的生活历史和社会变迁史。
二、走出“围龙”:追寻历史生命和灵魂
客家先民原来是中原士族平由于战乱,自秦汉以来,尤其是西晋以后大批南移,抵达江西南部,其中一部又迁移到闽西,有些人又从闽西迁至广东东部,即现在梅州山区,形成特定客家人群落,其特点是使用客家方言。他们的礼习多承传历史,保留中原古代遗风。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写道"荜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欲犹留三代前。"写出客家人的真谛。
客家人是一支特殊的汉族民系,它具有深厚的历也渊源和历史神秘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像黄遵宪、丘逢甲、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等这样一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书写出充满激情和生命的历史。
然而,用艺术形象来抒写撼动人心的客家民系充满血与火苦难历程的文学作品却从未出现。最近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程贤章的长篇小说《围龙》,它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客家人近百年来的苦难史、奋斗史和变迁史。作者是典型的客家人,他扎根在客家深厚的文化沃土之中,对客家人人文环境和勇于开拓与拼搏的历史有深切体验与理解。他在作品中通过近一个世纪客家风云人物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忍辱负重、坚忍不屈、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事迹描绘,让人们看到了被激活了的历史。历史在这里不再是僵陈闷郁的文字,而是被赋予了血肉、生命、激情和灵性,作者在叩问历史,追寻历史的生命和灵魂。
作者特地在扉页上说明"这是小说,不是历史。"其实,它既是小说,也是历史,正如田政委说的"进士第浓缩了客家人百年兴衰史。"作者正是通过客家人的围龙屋进士第的变迁来反映历史过程的。作者用记史的笔法,写出了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陈长修在南方策应康有为戌戍变法;陈长胜、陈长捷在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程武投奔程潜,参加东征、北伐,最后在淤沪抗战中牺牲;谢晋元、姚子青、黄梅兴等客家子弟在淤沪抗战中惨烈牺牲;"文革"中陈氏家族及烈士家眷袁来福等受到冲击,以及避居海外的陈氏家族回家乡办厂、投资等,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荡气回肠。在这里,历史变成活泼跃动的生命体;历史充满惊涛骇浪和复杂斑驳的颜色;客家子弟在这风云际会的历史进程中饱蘸生命的激情,书写着雄浑的历史,书写着生命史诗的篇章。
《围龙》反映历史,或者说折射历史,但不等于历史的叙说。《围龙》毕竟是小说,它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反映中国百年来的社会激变和由此引起的心理震荡,而且还在于它描绘出在历史变革中活动在社会舞台上的几代客家人物的形象。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把平面化的历史复活了,复杂化和立体化了,变得多姿多彩和具有丰富内涵,让人们去思索。19世纪英国历史李家麦芬莱说"历史,在它的圆满理想境界,至少是一种诗和哲学的合成品。它通过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动描述将真象印入人心。"(转引《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象征客家民系的围龙屋进士第大家族出来的陈氏子弟,在冲出围龙屋后,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而各奔前程,犹如汹涌的巨浪拍岸,折射出五颜六色的浪花。客家人是一个敢于冲击、敢于开拓、敢于拼搏的特殊的民系,他们不安于现状,不囡于陈旧固定的规范程式之中。所以进士第的几代人忧国忧民,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毅然以身报国;虽然有的远走异国,但"飞鸟恋旧林",最终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改以往致力于塑造某一人物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某种观念的程式,而是以写群体,造群像的思路来反映客家人的群体精神风貌,尤其在改革开放的特殊情境下,远走南洋的天送、省辉、韩辉以及客家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大野等回乡省亲投资,群贤毕至,群像皆活,使人省悟到有深厚文化意蕴的中华文化产生的巨大的融合力、亲和力和强劲的生命力。故乡的山水,故乡的田野和客家人的围龙屋……明月之思,家国情怀,把海内外的客家人凝聚在一起了:作者巧妙地写出善良、正直和充满活力的田政委的生动事迹,这种积极进取的力量凝聚了客家人的进取力,把当代的客家人的历史写得更生动了。田政委用他的宽容、热心和远见卓识,用他在"文革"、抗洪和招商引资中的特殊的行动语言,凝聚了走出围龙屋以后的海内外乡亲,抛弃前嫌,为建设新家园而共同合作,昭示出当今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
《围龙》是一部有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性和谐统一的作品。作者写历史、写人生都有强烈的社会价值、人生价值和伦理价值观念烛照之下来展示人们的价值取向;他审美,也审丑,把各人行为的正面品格与负面人生的复杂性充分揭示出来。例如,程武,他与田氏始乱终弃,作品对他在深山修行时的恶劣德性等负面人格作无情的鞭挝,同时对他走出进士第怪圈之后投身东征、北伐乃至投身抗日,在上海吴搬港率军抗战、英勇杀敌的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作了热情的歌颂。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再现的历史,雄浑的历史和鲜活的历史;而在改革开放后进士第的子孙们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又使人感奋不己,作者机智地把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来思考,营造出一种客家人的敢于抗争,为国家民族利益敢于拼搏、不惜牺牲生命的特质,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生命力和延续,呈现出时代生活的深刻的社会蕴涵。
三:生存与拓展:客家民系的文化品格
"围龙"是什么?
北方人把聚族而居的屋舍叫做"土围子",客家人则把它叫作"围龙屋"。《围龙》中的围龙屋颇有气派:无疑,在沿河上十里、下十里二千多户人家中,陈家的围龙"进士第"是这一行客家人聚集中最够气派和繁华的。它坐北朝南,后面以百亩果因为依靠,这座两层的围龙屋前面有一口十来亩的池塘,像拱月形揽住三堂四横的大宅舍。那结构极像北京的四合院。一百个房问,二十多个厅堂,气势甚为庞大。据说,可以扎下一个团的官兵。其规模和气派要比北京的四合院宏伟得多。
"围龙"是什么?它是客家民系象征的围龙屋,然而,它又是超越于围龙屋之外的围龙屋"。这是一部历史,一部客家民系特殊的历史:创业史、苦难史、悲欢史,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充满荆棘的社会前进的历史。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程贤章写围龙屋,他站在围龙屋里写围龙的客家人的"秘史",同时又跳出围龙屋来写围龙。他审视历史,透视现实,使他的艺术世界极其宽阔。他从客家人的南迁,到定居与创业,写出这座进士第围龙屋所表现出客家民系的神秘的生存力与坚韧的文化融合力。同时,程贤章又特意以浓墨重彩来写从辛亥革命到当今改革开放的政治风云,以家族史和家族文化为中心,淋漓尽致地描述客家民系的特殊地域文化蕴涵。
围龙屋进士第是客家人的民居特征,同时又象征着客家传统文化的具象,而进士第是客家人围龙屋的代表性建筑。为此,作者花了许多笔墨去描写。围龙屋是客家民系长期不断迁徙而形成的传统民居,它在客家人保护自己、抵抗外侮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这种有着特殊蕴涵的围龙屋形成客家文化的特有的亮丽风景线。作者写魏晋末年,中原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许多名门望族纷纷南迁,这就是中原汉民的大迁徙,也就是客家人的大迁移。作品写到南齐旺族程旻举家举族南迁到梅州,居山创业,施善行义,把中原文化与当地人的文化融合。多少年以后,程氏子孙陈氏家族在山居围龙屋里屋外,演出了忧国忧民、除暴安良、勇抗外侮的壮丽话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绘客家人的这些文化品格时,着重对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予以肯定,同时着意表述这些民族文化精魂在生生不息、顽强拼搏的客家人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仁"和"义"为儒家文化精髓,其实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爱人以仁"便成为客家人的行为准则。为此,居住围龙屋的客家人能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和相处。"仁"与"义"是互融互补的,行仁好义是客家人的文化传统。当外力欺侮时,程武、谢晋元、黄梅兴等客家子民,舍身求仁、弃家取义,义无反顾地奋勇杀敌,英勇献身,表现出客家人的高尚的民族气节,这实际仁也深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魂。正是围龙这种象征的民族文化精神,使客家子弟对中华民族的正义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与为追求真理前仆后继、敢于献身,为国家民族和客家民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围龙》中的围龙屋进士第是宗族文化的典型,作者对陈氏家族的浓墨描绘中,其实还淋漓尽致的描绘了宗族文化的隐秘景观。在客家民系辗转迁徙的艰巨而又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情,朋友有信,这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也是客家人恪守的人生准则。
围龙屋进士第里的陈长胜、陈长捷等为国捐躯,留下的陈长报是年长的族长了。在风雨如磐的漫长岁月里,陈长报经受了风风雨雨,但他死守围龙屋进士第,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客家人的守正不阿、树德务滋的品格。陈长报富于正义感,他曾经去过东南亚,回国后筹划办报反清;他与爱国华侨温生才有密切联系,并参与密谋刺杀两广水师提督李准。温生才事发失败后,他回家教书,在国共两党争夺厮杀中,两边不讨好,“国民党骂他白皮红心。共产党说他红皮白心,陈长报落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但陈长报凭良心做事,不雇工,不剥削,不搞土地出租,他遵循祖训,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办事,最后默默无闻死去。他竭力维护进士第这象征客家人文精神的祖产,体现了客家人遵循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这也体现出客家民系恪守祖训,想维护温饱和仁义礼邦的理想家园的人文精神。其实,在外战内争的过去,陈长报想维护围龙进士第,维护温饱平和的理想家园是难于实现的,陈长捷的无言死去就表明他这种保守型的最低理想也随之湮灭。作者以淡淡的叙述手法已经对陈长报作了否定。
在《围龙》中,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叙事,把对客 家民系的人文精神中的积极进取精神融汇到圆润的结局之中。这就是作者机智地对人与文化作出的耐人寻味的诠释。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演说中强调"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生存,他们还能继续发展","人是不朽的"。
人的永恒的生命价值和文化精神是,他们不但能在逆境中苟且生存,而且他们还能继续发展。正如鲁迅所说:人类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遍的人性,人的通性。客家人世世代代饱经患难,风霜雨雪严相逼。但他们知道生存的要义与法则;他们深谙生殖生存的深义,这就是延续生命和人文价值的重建。他们深知,"人是不朽的"。其内涵是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勇于开拓。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们有深深的蕴涵:人的创造力。
《围龙》不仅描述客家民系为了生仔发展而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正气,而且还写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在北伐中牺牲的老袁之子袁来福。在生活中并没有"来福",反之,绵绵而来的是苦难。他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医,日本战败后,一位日本军官剖腹自尽,留下儿子。袁来福与这位日本军官之妹信子结合,把日本军官的遗子收为义子,并带回家乡抚养,由此带来人生的悲喜剧。袁来福为此招惹了祸,解放以后政治运动无穷无尽的审查,"文革"中更是在劫难逃,后来由于中日建交,才改变其悲剧命运;由悲而喜。接踵而来的又是由喜而悲——悲喜交集:由于信子回国,带来家族的难题,而袁来福的儿子袁和平也经历了"文革"带来的苦难,但他却有很强的顺应时事能力和倔强生长能力,经过生活磨难之后,终于创造出人类的辉煌业绩。同样,进士第的陈长修在变法失败之后,逃到南洋谋生,衍繁后代,开拓事业,使后代天送、醒莲、韩辉等能在异国生根,从而有机会报效祖国,表现出客家人的顽强生命力。
落地生根,努力拓展,是客家人的特质。唯其如此,客家民系才能迅速从北到南,繁衍发展,而后又拓展海外,以致有这样的说法"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事业。"在南洋还有这样的评语"客家人开埠,广州人占埠,潮州人旺埠。"敢于开拓、善于开拓,坚韧不拔地生长发展,正是客家人的深厚的文化精神。程贤章在《围龙》中自觉地把握住这一客家民系的文化精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还值得一提的是,程贤章深谙客家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知恩图报的美德。他在作品中作了极精彩的诠释:袁来福的义子袁和平回日本后,也以客家人的发奋拼搏的精神创出了事业,他思念客家山区,回来投资,报答哺育他成长的第二故乡;韩辉是印度血统的弃儿,被天送夫妇收养,他成功创业后,也回到客家山村投资办厂,报答客家人的养育之恩。这里显示出作为中华文化的客家人的美德,连外籍血统的"客家人"都得其精髓,充分表现出客家文化精神的感人力量。
程贤章在对人性的挖掘和描写中.紧紧把握人与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客家文化环境对客家民系的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与影响,揭示出客家民系的艰难的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所显示出的具有独特意义的客家人文精神,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四、山与屋:客家文学的叙事基调
不久前,我在一篇评述潮汕青年作家陈跃子作品的文章《海与岸:潮汕乡土文学的文化意韵》中,把同处粤东,同是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汉族特殊民系而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作了比较"我常想同处于粤东的客家人和潮汕人的文化品格异问问题,概括地说,客家人地处山区,背山面山,围屋而居,视野较狭窄,走不出山与屋,其文化特征可归结为‘山屋文化’,而潮汕人则背山面海,视野开扩,出门则海,其文化特征可概括为‘海岸文化’。"
我以为,"海岸文化"是较准确地把握了潮汕文化的内涵,而"山屋文化"也准确地点明了客家文化的特征。背山而居,面山而行,向山而作,这是客家人祖祖辈辈难于改变的现实,正因为山穷造成人穷,穷则思变,必须向山地宣战,向大地攫取,才能生存。山是刚强坚毅的,人也是刚烈不阿的。客家人由山与屋造就的独特的文化心理,形成敢上天,敢下地,不平则鸣,不屈不挠的民系性格。
也就是说,"山屋文化"是客家文学的重要标帜。从客家文学史上看,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人的诗歌,张资平早期的一些描写客家人生活的小说,李金发的一些怀乡散文与诗,直至当代客家文学的奠基者程贤章的客家乡土系列长篇小说,都离不开山与屋以及由山与屋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客家文化,由此而奠定了客家文学在中国近代及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程贤章的《围龙》是当代客家文学的扛鼎之作。这是反映客家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交融出的写实作品,它写出了客家人厚重的历史和具有热力的现实生活,是客家地区深厚的沃土上产生的乡土文学,是发韧于历史、植根于现实的有着深厚功力的作品。中国乡土文学源远流长,它通过一个地域乡村的历史变迁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变化描绘,折射出过去与现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状态与文化意蕴,因而具有强劲的艺术生命力。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标示出乡土文学的地域特色和社会蕴涵,蹇先艾的《水葬》、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废名的《竹林的故事》、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以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写了作者的乡土情结和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当代作家刘绍棠的运河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古华的湘西系列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传品展示出急速变化的社会风貌,具有浓重的地域风情,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景线。可见一个作家如果用工笔重彩写出地域风貌的热烈颜色以及社会变革中的人情世态,就能产生具有长久魅力的乡土文学来。程贤章正是致力于描绘客家山川风貌、人情风俗以及展示客家社会历史情状的作家,他的系列长篇小说《胭脂河》、《彩色的大地》、《神仙?老虎?狗》、《云彩国》以及《围龙》等再现了具有客家韵昧的风土人情,有其独特的生活情境:山歌;情歌、水客、围屋、墟镇、山寺、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社会环境等,在程贤章笔下都作了绘声绘色的描摹。《进士第》中对围龙屋的描写,《"黑描"投胎》对客家种种神秘文化叙述,《老母山两"道士》对老少两"道士"的刻划,《宰狗》中对客家人焖糟水狗肉的细描,《跪乳》中对客家特有的子孝母亲养育之恩的体认等等,都深深地烙下客家乡土文学的印记,既有浓浓的人情昧,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呈示出美丽隽永的客家民俗的风情画,有着独特的韵味。
当然,乡土文学不仅要有厚重的地域文化色彩,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蕴涵。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说"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是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震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可见,乡土文学除了描绘特定的地域的社会风情外,还应该充分挖掘它的社会内涵,揭示其蕴含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这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命题。古华在《芙蓉镇》的"后记"中谈到他的作品是"寓政治风云于风情民俗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可以这样认为,古华的这种乡土文学观念是乡土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
《围龙》叙事基调是以进士第里外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通过进士第的兴衰荣辱描写,折射客家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反映他们命运的坎坷,生活的艰辛,它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史诗意识。进士第里的陈氏家族,在经历100多年的人世沧桑之后。留守围龙屋的也好,走出围龙屋的也罢,他们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令人震颤的活剧。无论留守围龙屋的陈长报,或投笔从戎的程武,抑或远走南洋的陈民利,他们是普通的客家人,又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客家人的命运。他们虽然个性各异,生活道路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有着共性:真诚、坦荡、执着、认真、倔强、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这些正是客家民系在千百年来形成的特点,体现出客家人的品格。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道路无不与政治风云、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维系在一道,这就使围龙屋进士第不仅仅有家族色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社会内涵。
由此可见,乡土文学需要准确把握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精神,尤其是要把握好这个地域的群体在特定的历也情境和现实社会环境中,由传统的文化积淀以及新的社会因素制约下产生的精神风貌,把握好一点就能较好地表现特定地域中产生的与时代风云相联系的社会生活,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程贤章的《围龙》紧紧扣住客家民系的文化精髓,与时代风云变幻联系在一起,使作品不仅有.时空的广度与宽度,而且有作品的厚度与力度,无疑这是乡土文学的新收获。
一方水土育一方的人。特定的地域由于其社会环境、民情风俗、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生活习惯等等,以及长期的历史环境会哺育出一方俊杰。乡土文学就要着意表现特定地域沃土上培育出来的有个性的人物,才能生动地表现时代生活的内涵。
在《围龙》中,程贤章给读者奉献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程武是颇具个性的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充满激情,以浓重的色彩描绘这个好坏兼而有之的人物。程武出生三个月便过继给舅母田氏为子,长大后与田氏乱伦,留下血脉后离家出走。他当了道士,但不安分的他与女信徒做了许多"不安分"的事;他从军,却仍不安分,近乎恶作剧地教训了作奸犯科的小恶霸,这些构成了他的负面人生;但他嫉恶如仇,对军阀吴佩孚的战斗中他智勇双全,率部战而胜之;当日寇战火燃烧到上海时,他英勇作战,奋勇献身,为国捐躯。作者写他与田氏始乱终弃,忘恩负义;写他与女信徒的浪漫情调等,但瑕不掩瑜,程武在时代的血火锻造下,终于完成他的光辉人格的塑造,表现出客家人敢于抗争不畏强暴,爱国爱家的刚毅性格。
在作品中,北伐牺牲的老玄之子袁来福也是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子承父业,到东北前线抗日杀敌。在偶然的机会中与信子结识后结婚,返回故里。按理说,他可以过夫唱妇随的平静生活,偏偏解放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波接着一波,这就造成他逆来顺受,安贫乐道的性格,但他弃农就副的经营方法与当局者的政策不一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于是在"文革"中产生了和县委"老走资派"站在一起陪斗的尴尬局面,但这一切使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凌辱的袁来福的性格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在批斗中,他不但没有自卑感、羞辱感,反而觉得有几分光荣。这种现象看似滑,其实是写出了时势造就的袁来福变态的个性,让人们掂出生活的分量。
大野(原名袁和平,是袁来福义子)是日军军官的孤儿,由袁来福收养,在客家山村长大,当中日建交后回到日本;韩辉是印度血统的弃儿,由天送、醒莲夫妇收养。大野与韩辉都是客家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他们成家立业之后,忘不了父母亲的恩德,更忘不了浓浓的故乡情,他们回报家乡,他们虽然个性不同,但却在报答知遇之恩上殊途同归,因而产生了鲜明的共性,让人们读到活脱脱的人物形象。
田政委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在他身上体现出客家人的美好品质;勇于开拓,敢于承担责任,为了众人的事业,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尤其在政治风暴席卷客家山城时,他运用他的机智保护了像大野等外籍人士。他默默无闻地工作。善于团结人,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团结海内外客籍人士,共同建设新家园。
程贤章在《围龙》中把客家人的大山一样的宽阔的情怀,大山一样刚毅的性格,与围龙屋所象征和昭示的客家民系深厚的文化根基联系起来思考,在审美态度上把人与环境、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放在强烈的时代色彩中加以整体观照,使人物体现出浓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当然,《围龙》并非完美无缺。由于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时空跨度较大,结构上难免有某些松散之嫌;由于作者偏爱叙述和议论,并以此来推动情节发展,有时显得沉闷;另外在写法上有些地方也略显粗疏。但从总体上看,《围龙》是有力度、有气势的作品,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较为成功的。